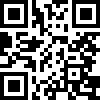1950年,张芝和朱曾汶在南京路国际照相馆拍的婚纱照

上世纪40年代末,亚美麟记两位股东苏祖国(左)和陈子祯(右)在电台大播音间

张芝和女儿朱宁、外孙媳妇赵令宾

中年张芝
 1948年,张芝在亚美麟记电台大播音间门口
1948年,张芝在亚美麟记电台大播音间门口 ◆张芝/口述 赵令宾/整理
张芝,新中国第一代女播音员。1929年生于北京,1939年举家迁居上海。1946年因父亲过世,就读高二的张芝辍学,成为私营电台女播音员。新中国成立后,进入上海人民电台播音组。1958年10月1日,上海电视台开播首日,张芝和男播音员陈醇在人民广场上搭档主播第一条电视新闻《1958年上海人民庆祝国庆大会和游行》。赵令宾,张芝的外孙媳妇,近年专心为外婆做口述实录,记录已然逝去的烟云。
应聘金都电台播音员
1946年,我17岁,念高中二年级,因为父亲过世,家里什么收入也没有了。上不了学,便在家听无线电打发时间。平日里,我最爱听一位叫施燕声的女播音员的声音。听说在新新公司的五楼有一个玻璃电台,施燕声就是玻璃电台里头的女播音员。电台外面一圈是吃茶点的,客人们可以边吃点心,边看女播音员的一举一动。我没有条件去吃下午茶,就整天守在无线电前听施燕声播放流行歌曲,那声音真是动人心弦。
一天,正听着无线电,突然从金都电台传来了一则招人广告。他们希望找一名讲普通话、略懂英语的女播音员。我便打算去应聘。我出生在北京东城,十岁的时候随家人搬来上海,虽然在新式里弄里学会了一口上海话,但说起普通话来还是一股子北京味儿。英语是在进彼得小学后学的,我的父亲据说在英国轮船上当过差,在家便老是用英语跟我说话。电台的面试官拿唱片叫我报名字,我不带犹疑地报着,他一听我这声音,一看又年轻,马上就录取了,每月六块钱工资。
起初的工作主要是播报台号和插播广告,因为电台主要靠广告来盈利。我坐在一个半玻璃的、像柜子一样的小播音间里,桌上摆着一套播音设备,一旁有两个唱盘,身后是一个放唱片的柜子。小播音间外是个大播音间,我坐在小播音间里既看得见也听得到外面的情况。大播音间的节目结束了,我就关闭他们的话筒,开小播音间的话筒报广告。比较出名的有家庭工业社生产的无敌牌牙粉、蝴蝶牌雪花膏,还有一些化妆品、香皂、牛奶公司和医药公司的广告。等下一档节目的人员都进大播音间准备就绪了,我再介绍这档节目的名字。
主持电话点唱节目
没多久,“友罗”洗发香波的老板找上门来,要求做一档播放外国流行歌曲的节目,他拿唱片来,很多都是电影插曲。老板让我负责这档节目,晚上7:00到8:00的黄金时段播出。这是一档电话点唱节目,不出几日,已红透了半边天,电话根本来不及接。来电的全是青年学生,圣芳济学院、圣玛利亚女中、震旦大学、圣约翰大学……这些学生就爱听外国的电影插曲。电话点播还有一个好处,身边的朋友谁过生日,可以为他们点唱。学生们都流行用英文名字,我在播音室外面接了电话,草草记下人名和歌名,就赶紧回小播音间里播报。一张78转的唱片,能放三分钟左右。旋律还没结束,外头的电话铃又响了。趁着前一张唱片还没放完,我赶紧在抽屉里“咵咵咵”地翻找,第几格是哪张唱片烂熟于心,抽出来就往录音机另一个盘子上摆好。
某月月底前的一个晚上,节目快要结束了,老板来了一个电话,通知我说这档节目就到今天晚上为止了,月底要换稚青女士教唱京剧。我一听,急了,这么好的节目,做得这么火,怎么能说没就没呢?接完电话,我马上就在广播里说出去了:“今天是节目的最后一天,要点唱的朋友赶紧来电话。明天没有了,明天老板要换更赚钱的节目上来了。”这一说,老板他们听见了。一会儿工夫,老板一个军界的朋友“蹬蹬蹬”跑上来,腰里别着枪,开口就说:“侬明朝勿要来了。”“勿来就勿来!”我就回他。回头打开话筒对听众说结束语的时候,又加了一句:“各位听众,咱们后会有期!”
从“金都”到“亚美麟记”
谁知道在家待了不到两个礼拜,亚美麟记电台通过亚洲电台的一位女播音员来找我了。据说那时候上海有百十来家电台,大部分是说沪语的。其中有八家是老牌的电台,由警备司令部管辖。“亚美”是无线电公司,“麟记”是蓄电池厂,还有“大中华”“大陆”“元昌”“鹤鸣”“东方”和“华美”。抗战结束后,因为受到国民党频率的限制,两家电台只能合用一个频率,所以亚美和麟记就成为了一家电台。面试当天,接待我的是苏祖国老板,他知道我在金都电台工作过,就随便问了几句,最后说:“我们需要你到这里来做播音员,你愿意吗?”我当然说愿意了。他接着说:“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。”于是,我就这样进了亚美麟记电台。
亚美麟记电台位于成都路静安寺路路口的一栋四层洋楼里,入口处是一条大楼梯,二楼是沧洲书场,三楼是福致饭店,电台在四楼。因为沧州书场的关系,洋楼总是门庭若市,评弹演员络绎不绝。最有名的要数蒋月泉,说的是《玉蜻蜓》,每天骑了一辆哈雷摩托车来演出。严雪亭说的是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,里面有一个桥段是审小白菜,要用普通话说,有些字音吃不准,他就来找我。张鸿声是说大书的,说《英烈传》的,有时候也要用普通话,我就给他矫正。还有刘天韵、薛筱卿、姚荫梅、唐耿良等等,他们用得上普通话的,都会来找张小姐。我在四楼播音的时候,人家都要上来看看张小姐。小播音间有窗帘,我一拉上窗帘,他们就看不见了。外面大播音间的上半截是玻璃的,下半截是白色的隔音板。许多演员下午先到大播音间演播,再到楼下书场演出,电台有时候也会转播书场的实况。
亚美麟记的节目很多,除了评弹,还有不少学术性、教育性、医学性和娱乐性的节目。老板们认为社会大众受教育的机会少,希望用这些节目来弥补这种不足。大清早,一位姓杨的老先生操着一口方言教古典文学理论。紧接着有魏超田老师教英文、庞京周医师的医学讲座、口琴专家石人望教吹口琴等等。最要紧的是老板陈子祯和红十字会合作推出的“流动诊疗车”,这辆车到处给人家义务看病,电台就帮忙宣传筹款。去了没多久,我就给电台加了一档外国流行歌曲。有了金都电台的经历,这档节目办起来熟门熟路,而且也非常红火。
因节目结缘终身伴侣
老板陈子祯的儿子叫陈治文,我们都管他叫小陈先生,是负责接广告的,也不知怎么地就跟华纳电影公司接上轨了。有一天,他来找我:“张小姐,我给你介绍个朋友。这个朋友是华纳公司的部门经理。”1947年,我还不到20岁。那个时候,我们跟大中华大陆合用一个频道,我们半天,他们半天。所以就在我半天休息的时候,小陈先生就把一位西装革履、谈笑风生的男青年请到电台来聊广告业务。这位男青年名叫朱曾汶,从大同大学英国文学专业毕业。凭着良好的中英文功底,毕业后被华纳宣传部门录取,23岁就晋升为了宣传经理。
和华纳的合作开始之后,我就要在西乐节目里插播他们的广告了。朱先生手下有一位专门撰写广告词的同事,哪个新片在哪里上演,导演是谁,男女主角是谁,配角是谁,什么乐队配乐,稿子是全英文的,每天写完就通过送差的送来。西乐节目安排在每晚的黄金时段,前曲播了一会儿,我把音量调低了,先播报几首点播的曲子,然后在关键位置报他们的广告,比如说,南京电影院将要在下个星期几,几月几日,上演一个新片子。男主角是阿伦·博雷茨,女主角是贝蒂·戴维斯。同时介绍贝蒂·戴维斯在电影当中的片段与表现,她过去演过什么片子。很多电影的片名,都是朱先生起的,比如:《出水芙蓉》《金石盟》。他认为片名取得好,吸引力就大,看的观众就多,票房价值就高。
为了吸引更多听众,我们在西乐节目里推出“幸运数字”活动。听众可以打电话或写信来点歌,同时申请一个号码。我们每星期抽奖一次,每次抽出十个号码,奖品是两张电影院花厅的电影票。电影票对朱先生来说是最不缺的,他在影院票台上一签字就行了。这样一来,节目就越发红火起来了。听众不单是来电话,来信的也很多。一麻袋一麻袋的信件,全送到华纳公司。华纳公司没有人手来拆信,朱先生就想出了一个办法,叫我们电台的两个播音员上门去拆信。一三五我做,二四六另一位播音员做。朱先生给车马费,又增加了我们的一部分收入。来信点播我就能事先安排了,根据来信内容,今天晚上要播哪个歌,是谁点给谁听的,我都写下来。当时的听众要想听一支歌,除非去买唱片,唱片是很贵的,不然就只能打电话或者写信到电台来点播,然后就在家里耐心等着电台播送的那一刻。所以说当时的听众更执着、更痴迷,也更可爱。
随着“幸运数字”日趋火热,我和朱先生也渐渐熟络起来。电影院是我们时常碰面的地方,有时因为听众的来信,有时因为新上演的片子。我们还会去石门路南京西路口的沙利文二楼喝咖啡,吃下午茶。有时候也去电台隔壁的仙乐斯舞厅跳舞。驻场的菲律宾洛平大乐队知道朱先生最喜欢哪支曲子,每次只要在舞池里发现了我们,接下来必定会奏这支曲子。朱先生从小住在同孚路333号他姑父家,步行就能到达亚美麟记。等我们慢慢地接触得比较密切一些了,他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到电台来看我播音。我的小播音间里有个小圆凳,可以坐一个人的。他就坐在小圆凳上看着我工作。
1950年6月8日,我和朱先生结婚了,我们找了美华酒家,就在石门路和斜桥弄的口子上。“美”是亚美麟记,“华”是华纳,倒也巧了。苏祖国和陈子祯是我们的证婚人。
今年是兔年,我已步入95岁高龄。回想起70多年前在玻璃盒子里的时光,就好像在昨天一样。这个狭小而透亮的盒子,是我梦想的起点,它用电波把我和千家万户相连,开启了我一辈子的广播事业。
也是这个狭小而透亮的盒子,让我和朱先生悄然相遇,携手走过了一段永远年轻美丽的钻石情缘。